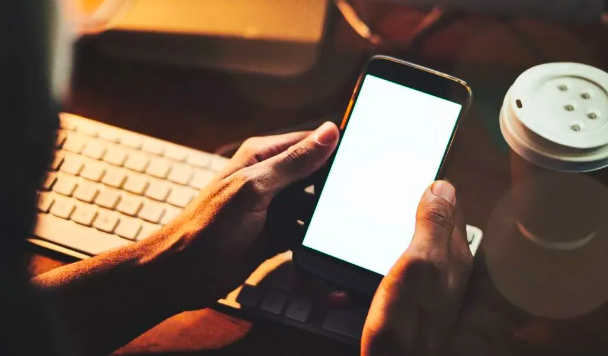刚过2021年元旦,欢喜传媒集团就宣布与芒果tv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协议内容包括在“芒果TV”手机APP及湖南快乐阳光运营的湖南省运营商互联网电视业务的全部终端设立“欢喜首映”专区,从内容专区所产生的的收入经扣除相关成本后由双方进行分成,战略合作协议为期三年。
前不久,在2020年12月11日,欢喜传媒集团就曾宣布其与华为、小米达成战略协议,将在小米电视、小米手机和华为电视、华为手机上设立“欢喜首映”专区,产生的利益同样由双方分成。
欢喜传媒如此看重欢喜首映的原因是什么?与这么多渠道方合作,能让欢喜首映成为国内顶尖的流媒体平台吗?
把控内容靠“合伙”
欢喜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在影视行业中,很明显处于上游位置,可以归属于内容生产方。在内容生产把控方面,欢喜传媒有一套自己的模式。
2015年,欢喜传媒由董平、宁浩、徐峥和项绍琨联合创办,宁浩、徐峥在2015年入股时分别占据19%的股份,是第二大股东。
宁浩徐峥这两位明星导演,作为股东自然是要为自家公司发展出一份力。两人分别与欢喜传媒签有6年合约,合约内容包括每三年导演一至两部电影作品,欢喜拥有他们作品的排他投资权及制作权,以及大中华地区各渠道的优先发行权。
这一合作模式被欢喜传媒称为“导演合伙人制”。欢喜传媒凭借这一合作模式,采用股权或者合约的形式,绑定了很多优质的导演,打造出欢喜传媒的“导演天团”。
欢喜传媒的股东导演除去宁浩、徐峥之外,还有王家卫、陈可辛、顾长卫、张一白、张艺谋,非股东导演有王小帅、贾樟柯、文隽、李扬、陈大明、刘心刚。
内容是内容行业存在的基础,掌握了导演也就掌握了在内容行业的主动权。对于欢喜传媒来说,“导演合伙人制”保障了高质量内容的供给;对于导演来说,拥有股权激励和预订投资,在创作时更有积极性,更具自由度。欢喜传媒在内容供给端让创作者(导演)们有利可图。
另外,欢喜传媒的7位股东导演中,有4位导演的合约中有网剧项目。从这点可以看出,欢喜传媒的内容形式不仅仅局限于电影,通过与导演进行股权绑定和合约限制,欢喜传媒还进行了新的内容形式拓展,从这点可以看出欢喜传媒的目光很早就不只局限于电影。
不过欢喜传媒也为“导演合伙人制”付出了很大代价。
2016年,欢喜传媒为王家卫、陈可辛、顾长卫、张一白四位股东导演配发新股产生非现金开支11.20亿港元,当年企业亏损12.54亿港元;2018年欢喜传媒与张艺谋达成合作,配发1.5亿新股产生2.7亿港元非现金开支,当年企业亏损4.45亿港元。
对比2015年、2017年欢喜传媒财报显示的九千多万港元亏损,2016年、2018年受到为股东导演进行增股绑定的影响,亏损金额实在有些高。
掌控渠道靠合作
影视行业可以简单分为内容生产方、发行方、渠道方,内容生产方负责提供内容,发行方负责宣传,渠道方则负责将内容呈现在消费者(用户)面前。欢喜传媒作为内容生产方,主要依赖的渠道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线下+线上。
对于欢喜传媒来说,电影在线下影院上映,欢喜传媒作为投资出品方可以获取票房分账收益,是最为传统的内容渠道变现方式。不过,欢喜传媒在线下渠道的变现上,喜欢与发行方搞“合作”。
就拿近两年的春节档电影来说,2019年春节档,欢喜传媒独家投资、宁浩导演的《疯狂的外星人》与发行方乐开花影业签订28亿元保底协议,虽然最终保底失败,但欢喜传媒依旧获得7亿元人民币收入,远超之前其他电影的收益。
2020年春节档,欢喜传媒独家投资、徐峥导演的《囧妈》也曾与横店影业签订24亿元保底协议,欢喜传媒本来通过这次保底将获得6亿元人民币收入,同时横店影业负责电影的宣发费用。不过由于疫情等原因,欢喜传媒选择放弃保底协议,与字节跳动达成6.3亿元合作,《囧妈》在西瓜视频上线。
在线下渠道,对于某些热门影片,欢喜传媒选择与发行方合作签订保底协议,获得较高收益。2019年欢喜传媒之所以能够扭亏为盈,除去参与出品的《我和我的祖国》获取的高票房之外,独家投资的《疯狂外星人》的保底协议带来的利润也是关键。
电影在线下影院上映之后,会在线上平台上映,在线上渠道方面,欢喜传媒比较传统的变现方式就是将影视版权卖给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一类的视频平台。而这一模式随着自家流媒体平台欢喜首映的推出,以及与各个渠道的战略合作,让欢喜传媒在线上渠道的变现方式大致演化为两类。
一类是欢喜传媒利用内容换取渠道方出钱进行合作。
例如2018年7月与2019年3月猫眼娱乐入股、认购欢喜传媒股份,获得欢喜传媒主控电影、网剧的独家宣发权;2020年1月,字节跳动6.3亿元获得《囧妈》;2020年8月,B站5.13亿港元入股欢喜传媒,获得网剧《风犬少年的天空》、《夺冠》等头部内容。
一类是资源置换,欢喜传媒提供内容,渠道方提供平台,设立“欢喜首映专区”,所获收益双方分成,与线上渠道方合作通过欢喜首映进行变现。
与猫眼、字节跳动、B站达成合作之后,合作内容还有在合作渠道平台内设立欢喜首映专区。再加上欢喜传媒近期与华为、小米、芒果TV达成的合作,另外还曾与CCTV6旗下的1905电影网、百事通达成合作,合作内容都包括“开设欢喜首映专区,所获收益双方分成”。
不过,欢喜首映上线的时间并不长。欢喜传媒在2017年开始内测自己的流媒体平台“欢喜首映”,在2019年3月份才开始试运营。主要采用“会员制观看+付费点播”的形式,用户需要付费才能观看影片,借此来变现。
欢喜传媒CEO项绍琨在前几天接受36氪专访时曾提及欢喜首映的一些数据,欢喜首映的APP下载量已经达到了 2700 万,付费用户也达到了 500 万。这一数据对于国内主流的长视频平台来说,并不算高。而且,对于欢喜来说,线下渠道的收入远高于线上流媒体带来的收入。
然而,欢喜传媒的合作方包括票务平台、视频平台、手机、电视硬件场景,从多渠道、多场景、多维度支持自家的流媒体平台欢喜首映,为其吸引流量。为什么欢喜传媒要如此支持欢喜首映呢?
流媒体是大势所趋
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期间,线下电影院停摆,《囧妈》率先进行了“院转线”,此后很多影片跟随《囧妈》,放弃院线,转投线上渠道。
国外疫情仍然严重,纽约时间2020年12月3日,华纳兄弟宣布2021年其公司出品的17部影片取消窗口期,将在院线和流媒体平台HBO Max同步上映。
“院转线”、“流媒体”、取消窗口期这些趋势似乎是疫情导致的,不过,对疫情之前的影视行业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趋势其实早就存在。
“窗口期”指的是从电影上映到做成正版影碟、上线线上平台之间的时间,这一机制的安排是由于版权的边际成本递减效应,可以保证院线、版权方的收益。
然而随着国内长视频平台之间的竞争延伸到影视版权,以及一些平台资产参与到影视制作环节,平台影响力越来越大,长视频平台为了能尽早上映院线电影,窗口期越来越短。
2019年上映的《逗爱熊仁镇》,2018年上映的《二十岁》,窗口期只有6天。《北方一篇苍茫》是9天,《江湖儿女》上映13天就转到线上。这类窗口期缩短的例子还有很多,甚至有些电影尚在影院上映时,已经全网上线。
其实,窗口期也是版权方、院线方、线上渠道之间的利益博弈的体现。而缩短的窗口期也证明了线上渠道正在一点点赶超线下院线。
欢喜传媒洞察了这一趋势,所以对自己的流媒体平台欢喜首映极其重视。
不过,欢喜首映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
流媒体平台属于内容平台,形成平台的关键条件就是内容供给端能否大量且持续供给,以及让内容供给端创作者获利。欢喜传媒虽然能凭借“导演合伙人”制度保证欢喜首映的高质量内容供给,以及让导演获利,但是欢喜首映的内容不是“大量且持续”的。
电影、电视剧拍摄周期本身就很长,再加上欢喜传媒签约导演时间大多是6年,在2021/2022年左右就会结束合约,未来两年可能会是欢喜传媒的“内容爆炸期”。
就算可能会迎来欢喜传媒的“内容爆炸期”,欢喜首映的片源依旧有限。目前,欢喜首映平台上除了欢喜传媒制作的剧集,就是一些国外的经典电影或纪录片。对比国内头部长视频平台爱优腾芒,甚至西瓜、B站这两个中视频平台,影视版权资源库都相较于欢喜首映多。
而在影视版权的争夺上,需要大量的资本支持,欢喜首映获得的资本支持显然弱于国内头部视频平台。
天眼查APP显示,欢喜传媒自2015年成立之后,仅有猫眼、B站两次融资。根据雪球网数据显示,欢喜传媒的市值在50亿港元(41.64亿元人民币)左右,市值与爱奇艺、B站一类的视频网站平台相差甚远。
除去内容不能可持续供给,由于欢喜首映的会员制、付费观看门槛,欢喜首映由渠道方吸引过来的流量难以留存。
同时,欢喜传媒也不能保证这些签约导演拍摄出的一定的高质量内容。《囧妈》的豆瓣评分只有5.9分,与一些导演签订的合约中,部分网剧包括联合监制,若只是挂名,或许会影响欢喜首映的口碑。
而与欢喜传媒签约的导演也有自己的工作室,不会只根据欢喜传媒的合约拍摄影视。例如张艺谋导演的《一秒钟》上映之后,接下来还有电影《坚如磐石》《悬崖之上》,而张艺谋与欢喜传媒签订的合约还剩两部网剧,显然张艺谋导演并没有急于执行合约的网剧计划。
结语:
欢喜传媒与导演合作保证内容,与渠道合作保证变现。虽然认清流媒体平台将是未来的趋势,但由于国内视频平台的竞争环境,欢喜传媒只能从多场景、多渠道支持自己的流媒体平台。
不过,欢喜首映与太多渠道合作,除去一些特定合作方的内容,已经大大降低了其内容的“独播性”,让与其合作的平台也失去了内容方面的竞争力。
现在的欢喜首映,仅仅只是为了欢喜传媒能增加一种线上变现方式,同时,为以后线上渠道能盖过线下院线做准备。不过,到了那时候,欢喜首映或许会直接面对国内其他视频平台进行竞争,欢喜传媒还能做到长袖善舞、游刃有余、欢欢喜喜吗?